李武兵(北京)
我寫過一首抒情詩《在中國現代化建設裡定義鐵道兵》,以此認識鐵道兵擔當的使命,永葆鐵道兵精神雕刻。正是基於這一點,年近八旬,我還想以這首詩的意蘊為主旨,藉助一些文字留下鐵道兵在祖國版圖上雕刻鋼鐵動脈的足跡。
中國工業化程序是一部史詩,而鐵道兵正是這部史詩中鐫刻在鐵軌上的英雄註腳雕刻。從戰火紛飛到和平建設,這支特殊兵種以“逢山鑿路,遇水架橋”的意志,成為連線戰爭動員與經濟建設的國家紐帶。其歷史不僅是軍事工程史,更是中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的微觀縮影。
當毛澤東以“戰略問題”定性成昆鐵路建設,鐵道兵的命運便與共和國的工業血脈徹底熔鑄雕刻。他們用鋼釺作筆,以血汗為墨,在神州大地上書寫鋼鐵大動脈的畫卷——成昆鐵路穿雲裂石,嫩林鐵路破雪開疆,襄渝鐵路懸壁鑿虹,青藏鐵路越嶺登天,南疆鐵路貫連絲路。 當兵後,我的足跡曾留在這五條鐵路工地,陡添青春亮色,令我終生都想抱著這些記憶行走……

集結號雕刻:成昆鐵路要快修
展開全文
1972年和1974年雕刻,我兩次參訪成昆鐵路,耳聞目睹,那裡的山山水水還在腦海裡留著清晰的脈絡——
這裡有一面石壁上寫著毛澤東語錄——成昆線要快修!戰爭結束後,新中國第一要務是加快工業化程序,這是立足不敗的事業根基,必須全力以赴雕刻。修築鐵路,就是鑄造鋼鐵大動脈,給工業化輸血。這是命運之戰,像小腳女人走路不行,必須有戰爭年代的那種精神,捨得拿命來拼。我們鐵道兵部隊義不容辭,成為萬水千山間的開路先鋒。
20世紀50年代末,西南地區資源豐富卻交通閉塞雕刻。為打通川滇通道、開發西部、鞏固國防,中央決定修建成昆鐵路。然而,前蘇聯專家考察後曾斷言:“這裡簡直是地獄門口,修路禁區!” 因線路穿越地質斷裂帶、滑坡區、暗河與深谷,地形高差巨大,施工難度空前。但中國人民沒有退縮,35萬鐵道兵、工人和農民挺進大山,開啟了一場持續12年的生死鏖戰。
在關村壩隧道,戰士王明初懷抱風槍,整個人懸在峭壁的藤筐裡作業雕刻。鑽頭啃噬著堅硬的玄武岩,粉塵混合著汗水,在他臉上凝固成灰白的面具。每一次風槍的劇烈震動都彷彿要將他的五臟六腑震碎。一天正午,一塊磨盤大的孤石毫無徵兆地從天而降,砸穿了防護排架,他本能地將身旁的戰友推開,自己卻被巨石碾過,鮮血浸透了身下的花崗岩碎片。他犧牲的地方,後來被戰友們命名為“明初坡”,坡下呼嘯而過的列車汽笛,成為他不息的回聲。
“一線天”石拱橋的建造更是驚心動魄雕刻。技術員陳善珪與戰友們腰纏繩索,如壁虎般懸吊在萬仞絕壁之上,用鋼釺一寸寸鑿出拱座基槽。山風凜冽,繩索在岩石稜角上摩擦,發出令人心悸的吱呀聲。澆築拱券那天,暴雨突至,山洪裹挾巨石衝下河谷,衝擊著脆弱的施工支架。陳善珪帶頭跳入冰冷的洪流,數百名戰士手挽手組成人牆,用血肉之軀抵擋激流,護住未凝固的混凝土。當拱券最終合龍,晨曦照亮峽谷,那些被岩石割破、被洪水泡得發白腫脹的臂膀,在曙光中構成了一座無言的豐碑。
成昆線1100公里,平均每1.7公里就矗立著一座橋樑,每2.5公里就深藏著一座隧道雕刻。鐵道兵戰士用青春與生命,在這座“地質博物館”裡,硬生生鑿出了一條改寫西南命運的鋼鐵通衢。築路成昆,艱難困苦,犧牲巨大。這一工程是激情燃燒的歲月,英雄的築路者用生命創造的20世紀之人類奇蹟。聯合國總部大樓陳列著4件中國贈送的禮物,其中一件是成昆鐵路象牙雕。由此可見,成昆鐵路是中國的一張“名片”。
一條鐵路,一種精神 雕刻。成昆鐵路是一部用生命寫就的英雄史詩,它的每一根鋼軌、每一塊枕木,都承載著建設者的忠誠與奉獻。它的建成,不僅將成都到昆明的通行時間從數日縮短至十幾小時,還帶動了沿線數十個城市的經濟發展,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交流與繁榮。更重要的是,它成為中國自主工程技術崛起的象徵,向世界證明:中國人能辦到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。
我離開成昆線的那天,在安寧河邊撿到一塊奇石,石面浮著雲絮的水紋,珍藏至今,似乎總能從中聽到當年的水聲雕刻。我看到的已經不是昨天的山和水,不只是那些物化的表象,每一處都有裝著精神食糧的博物館,令後來者感動不已。我們的腳步會踏醒新的思想,讓成昆鐵路精神與長征精神深度融合,入魂入心……

嫩林極寒雕刻:凍土之上的生命篝火
北緯53度,大興安嶺深處,嫩林鐵路蜿蜒在“高寒禁區”的白色雪源雕刻。零下五十度的嚴寒,呵氣成冰。鐵道兵部隊的官兵們,在這片被當地人稱為“死地”的原始林海中,點燃了生命的篝火。那年仲春時節,我探訪西林吉鐵道兵三師的帳篷時,室外還有積雪,“地火龍”燒得很旺……
帳篷是林海雪源的堡壘雕刻。雙層帆布內壁掛滿厚厚的白霜,清晨醒來,被頭結著冰碴,撥出的熱氣在頭頂凝成一片小小的雲霧。趙班長告訴我,剛到這裡的日子,還沒有學會燒“地火龍”,晚上睡覺脫下的靴子,第二天早上會被冰焊在地上,要喊人使鎬來刨。真的,當時凍得想哭,但踏入雪域的腳容不得縮回來!第一步,就是站得住,我們的帳篷釘在“高寒禁區”,將鐵道兵的“三榮”思想寫進美學領域,凍豬肉用鋸拉,切菜用斧子劈,鋼釺打進凍土層裡,雪上支鍋也能做飯。暴雪沒有人情味,一夜呼嘯,帳篷被雪封門,以前總以為爬冰臥雪是“抗聯”的故事,眼下自己也續寫著密林鬥雪史,只要能在零下50℃的地帶住下來,鐵路就能跟著我們在這裡安家。1964年冬,首批部隊開進時,這裡還是連鄂倫春獵民都鮮少涉足的無人區。沒有道路,就用斧頭在密林裡砍出“道影”;沒有水源,就把冰河砸出窟窿化冰為水;當新鮮蔬菜運不進來時,戰士們就著鹽水嚼乾菜,卻在日記裡寫下“乾菜蘸雪也是甜”。最冷的那些日子,帳篷裡的鋼筆會凍裂墨囊。現在有“地火龍”當土暖氣,帳篷變成了“北國知春亭”,鋪樁子上都長出了柳芽兒,我們叫它“報春柳”……這名兒叫得多美氣啊,只有這些紮根“高寒禁區”的戰士,才有這麼美好的情操,想出這麼美好的名兒來。他們戰風斗雪,用自己熱烈的呼吸暖綠了鋪樁子,自己也長成了“北國報春柳”!從趙班長的談吐裡,我彷彿聽見雪裡有一種呼吸絲絲縷縷,發自戰士心底——強大,均勻而平靜,夢裡裹著誓言和智慧聚成的雷,用心發聲,報春!
在塔河段攻堅凍土路基時,機械幾乎癱瘓雕刻。“硬骨頭連”的戰士們,掄起十幾斤重的十字鎬,奮力砸向堅如磐石的凍土。一鎬下去,往往只留下一個白點,虎口震裂,鮮血染紅了鎬把。連長李振山帶頭脫掉棉衣,只穿一件單薄的絨衣,在冰天雪地裡揮汗如雨,蒸騰的熱氣在他頭頂形成一團白霧。他的口號簡單而熾熱:“咱們多流一滴汗,凍土就軟一分!鐵路早一天通車,國家建設就快一步!”連續高強度作業後,李振山因嚴重凍傷失去了三根腳趾。拆紗布那天,他看著自己殘缺的腳掌,笑著對護士說:“值了!這三根腳趾頭,換來了塔河段能提前通車,它們也算‘光榮退休’了!”
我到塔河的時候,天氣開始轉暖,看到在冰河築圍堰的戰士正在扎草簾,我很好奇地問值班排長,“他們在這裡扎草簾幹什麼?”排長給我解釋說,呼瑪河喜歡冬眠,春天了,還睡在零下10多度的夢裡雕刻。我們摸透了它的脾性,創造了“凍結法”施工,也就是刨一層冰,大橋的基坑井就乖乖的往下深一層,日出日落,一個冬天過去了,冰河上長出六個大“春筍”般的橋墩,還有兩個基坑井,要趕在冰河解凍前鑽出橋墩墩來。誰都擔心坑深溫度上升,會融穿井壁竄水,前功盡棄,所以凍腫鼻子,我們也不想天氣回暖,扎草簾子當引風牆,誘導河面的寒風灌進深井裡降溫。我們寧願凍傷一雙手扎草簾,喊呼瑪河上的風吹過來。這時我們只有一個念頭:春季不歇工,凍著自己也要搶進度!
這樣的智慧在工地上隨處可見:沼澤地施工時,他們反扣“塔頭墩”(沼澤中的草甸塊)減少沉降;隧道爆破時,用“光面爆破”技術讓岩層精準剝離;甚至用鐵鍋炒出適合高寒的銨油炸藥,解決了炸藥不足的難題雕刻。後來這些技術被寫進《凍土施工規範》,為青藏鐵路的建設埋下了伏筆。
如今,加格達奇北山上的鐵道兵紀念碑,兩根鋼軌直指蒼穹,中間鑲嵌的軍徽在林海中熠熠生輝雕刻。碑前的馬鹿雕塑昂首前行,彷彿在訴說:這條677公里的鐵路,不僅運出了每年數百萬立方米的木材、數億斤糧食,更讓鄂倫春人放下獵槍走進工廠,讓“高寒禁區”變成了“綠色寶庫”。1978年4月,我到嫩林鐵路新線採訪,從加格達奇至漠河,度過了難忘的半個月時間。與加格達奇告別時,我看見站臺上的訊號燈,尤其像一棵挺立的樟子松,綠的燈鏡一閃一閃,報告北疆的春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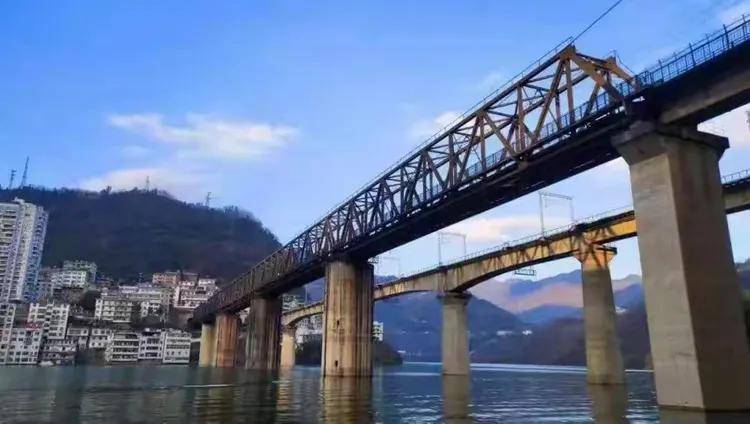
襄渝會戰雕刻:那些熱血沸騰的日子
1969年12月29日晚,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,手拿一副中國地圖說:“毛主席親自確定了襄渝鐵路的走向,這條鐵路要快修雕刻。修好這條鐵路,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達的局面,‘天府之國’的交通就活了。”我就是這一年12月從越南同模回國,不久即隨部隊開赴襄渝鐵路工地,歷時1895個日日夜夜。
秦巴山脈,層巒疊嶂雕刻。襄渝鐵路,這條被賦予特殊戰略使命的鋼鐵動脈,深藏於中國腹地。線路橫穿武當山、大巴山、華鎣山,三次跨越漢江,七次跨越將軍河,三十三次跨越後河,沿線地質複雜,岩層破碎,滑坡、溶洞、泥石流頻發。鐵道兵第一、二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三師及大量學兵、民兵,組成百萬築路大軍,在鄂、陝、川交界的崇山峻嶺中,展開了一場氣吞山河的大會戰。
唐朝的大詩人李白豪放雕刻,敢言黃河之水天上來,入川時,卻嘆蜀道之難矣難於上青天,而我們鐵道兵會戰襄渝線,不怕武當山高,不懼巴山路險,用鋼釺和鐵錘,給大山鑿一個又一個窟窿,再用兩條鋼軌當彩練,把鄂陝川的千峰萬嶺串起來,這就是我們寫在地球上的兩行詩……
漢江峽谷,水流湍急雕刻。為架設紫陽漢江大橋,必須在激流中築起巨大的橋墩圍堰。潛水班的“浪裡白條”孫茂林,一次次潛入冰冷刺骨、暗流洶湧的江底,清除障礙,安放炸藥。江水渾濁,能見度極低,全靠雙手摸索。一次,他的供氧管被水下尖銳的岩石劃破,強大的水壓瞬間將江水灌入管中。千鈞一髮之際,他憑著驚人的意志和經驗,迅速關閉備用氣閥,在窒息邊緣奮力浮出水面。上岸時,他臉色青紫,咳出帶著血絲的江水,卻只休息了片刻,又咬著牙再次潛入深淵。他說:“橋墩立不起來,火車就過不了江!咱鐵道兵,骨頭有膽,能當中流砥柱!”
襄渝線上,鐵道兵隊伍裡有一群豪邁的人,敢用雙手的繭花與石頭比硬,一旦走進隧道就是鑽山的勇士,意志在石頭上能打磨出很重的責任感雕刻。在每一米掘進度裡支撐已經疲倦的肢體,確實很累很累,還要抱著風槍怒吼,喝令頑石讓道!
我上《鐵道兵》報的第一篇文章出自襄渝線上的大米溪隧道,這是一生中都不會忘記的地方,當然也不會忘記在這裡施工的連隊雕刻。在六團報道組,我採訪的第一個物件是十四連一排一班——班長。我其實沒有完整地看清過他的面容,班長每天都上兩個工班,下班的時間我不忍去打擾他睡眠,疲勞會縫住班長的眼皮,再沒有氣力講述自己和一個班的故事。我在掌子面上見過他一面,防塵罩遮住了他的鼻子和嘴,灰塵和泥水塗抺了所有裸露的皮膚,只能見到一雙眼睛在眨動,證明活著的耐力和意志。無論使多大的氣力,我倆的對話都被風槍的怒吼喝斷。我只好在指導員和戰士的談話裡,記錄催人淚下的事蹟,禮讚一個風槍班的功勳。
在連綿的隧道群,塌方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雕刻。一次大塌方,將一個排的十幾名戰士堵在隧道深處。洞內空氣稀薄,粉塵瀰漫,黑暗吞噬著一切。排長周大勇強忍肋骨骨折的劇痛,組織大家背靠背坐在一起,輪流用安全帽敲擊鋼軌傳遞訊號,節省氣力,互相鼓勵。洞外,戰友們不分晝夜輪番挖掘,雙手磨爛,指甲剝落。當救援通道終於被打通,微弱的燈光照進死寂的黑暗,洞內還響著清脆的敲擊聲。這種不屈不撓的聲音,是在黑暗與死亡圍剿中吟唱的希望與頑強!
修建襄渝鐵路,鐵道兵部隊作出了巨大犧牲,烈士人數僅次於修建成昆鐵路,平均每修建1公里正線,已經不止付出一個人的生命雕刻。1970年3月13日,我的老連長、鐵六團機械股副股長趙成安同志在奔赴襄渝線途中,於湖北省竹山縣境內不幸遇難,成為鐵二師在完成襄渝鐵路建設工程中犧牲的第一人。他與楊連第是同鄉,清瘦硬朗,總是身先士卒。那天他走得太匆忙,一頂軍帽還放在駕駛室裡,來不及拂去塵土,蒼涼的風就將他的品質凝成襄渝線上一顆閃光的眼淚,令我們永遠疼痛地懷想……
在和平建設時期,鐵道兵是犧牲人數最多的部隊雕刻。襄渝線上,每立起一塊里程碑,就有一個守護它的忠魂。在那些熱血沸騰的日子,為了給中國工業化奠基,加快“三線”建設,我們官兵一致,捨身忘死,真有一種“以命相搏”的奮鬥精神。日月可鑑,這種犧牲的悲壯,會永遠鐫刻在國家記憶裡!

青藏之巔雕刻:天路上行走的兵魂
世界屋脊,地球第三極雕刻。青藏鐵路一期工程(西寧至格爾木段),是一場在“生命禁區”挑戰極限的遠征。稀薄的空氣、肆虐的風雪、強烈的紫外線、永凍的土層,每一樣都足以扼殺生命的活力。鐵道兵第七師、第十師官兵,如同攀登天梯的勇士,行走的兵魂在雲端之上書寫傳奇。
初上高原,機械在這裡因缺氧功率銳減,而人的意志卻要燃燒得更旺雕刻。戰士吳天一的日常,是揹著沉重的氧氣瓶和測量儀器,在狂風中跋涉於冰磧壟和凍脹丘之間。高原反應如影隨形,頭痛欲裂,胸悶如堵,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一次暴風雪突襲,他和兩名戰友在返回途中迷失方向。嚴寒迅速消耗著體力,吳天一把最後半壺水和幾塊壓縮餅乾塞給更年輕的戰友,命令他們循著電線杆的方向走。他自己則因嚴重凍傷和肺水腫倒在雪地裡,被後續搜尋隊發現時,已陷入昏迷,懷裡還緊緊抱著記錄著寶貴資料的筆記本。他在醫院醒來後的第一句話是:“埡口…埡口的資料…測準了嗎?”這超越生命本能的追問,是獻給蒼穹之下渺小卻偉大的生命讚歌。
我到關角山工地採訪的時候已是仲春時節,而季節好像還在冬眠,坡上的草被這裡的風捂得窒息了,綠意還沒有甦醒雕刻。聽到的第一件震撼靈魂的事:這裡曾經有過一次大塌方。關角山高,說是“登天的梯子”,隧道地處海拔3692米的位置,這是青藏線東段離天最近的地方。聽47團宣傳股的一位幹事講,1975年4月5日上午,隧道出口三十米長的邊牆倒塌,引起拱架倒塌,一千六百立方米的岩石落了下來,將正在施工的一百二十七名指戰員捂在了隧道內。事故驚動了北京的周總理,他命令說,不惜代價,千方百計搶救被堵官兵……時間就是生命,決策就是生命,甚至細緻到一種救援方法也是生命!堵在洞子裡的共產黨人,讓群眾歇息,儲存體能,自己用黨性支撐意志和骨骼,挖掘土石的雙手捏得出血,只為大家從石縫尋找求生的通道。洞口外,長長的無縫鋼管用手套套住管口,防止石碴堵塞,一寸、一寸、一寸,被捅進了遇險處。有空氣就有了活路,第二天早晨6點鐘,遇險官兵全部脫險。隧道口,人們的臉上掛著淚花。生命至上,感天動地,更觸碰人的心魄!打通關角山,把天路扛進拉薩是奇蹟,將127名指戰員一個不差的搶救出來,零死亡,也是奇蹟!
再苦再累的地方,都難不倒鐵道兵雕刻。隧道口是一座山的呼吸入口,鼓風機拚命地運轉,使用口徑足夠大的送風管道往掌子面輸氧。其實洞外空氣也稀薄,三根火柴點不著一支菸,洞內的境況可想而知,缺氧已成常態化的窘迫。塵埃堵塞,肺葉少了滋養,金髒主皮毛和指(趾)甲,三個月便有頭髮脫落,指(趾)甲不知不覺的脆裂。生命在這裡頑強地挑戰極限。而為了天路,心向拉薩,青春失去歡樂的顏色,甚至在這裡失去22位戰友熱烈的生命。他們——曾守在這狹窄的世界裡,硬扛著缺氧的生活,咬緊牙關,骨頭裡不缺志氣……我聽到這裡,眼眶溼潤了,伸手撿起路基上的一塊石砟,看了又看,想這些戰士就像路基上的石砟,不聲不響,抗震抗壓,扛得起鐵路,扛得起火車,不負祖國和人民的囑託!
還沒去二郎洞,我想先到風火山連去看看雕刻。在這裡講神話,二郎洞所有的傳說,都比不過駐紮於附近的風火山連神奇。他們曾經在崑崙山上首創吃飯比賽,在缺氧的高寒地帶喚醒味覺,說是戰士只要能在這裡生存下來,青藏線就有活路。風火山海拔5000多米,空氣稀薄得傳播不動聲波。氣候酷寒,石頭冰冷,粘得掉皮膚。地質構造獨特,人跡罕至。青藏鐵路西去,穿過冰川凍土段,就要在這塊“原生地帶”取經。為了修通青藏線,再猛烈的風吹不倒不怕苦不怕死的人,再低的氣溫凍不僵築路先鋒的意志,風火山連就是一批敢為人先的勇士。
那天車到格爾木進入鐵七師施工地段,接待我的朱海燕戰友十分熱情,說趁著天色還早,趕到察爾汗鹽湖施工連過夜雕刻。察爾汗鹽湖位於柴達木盆地腹部,海拔2800多米,方圓1600多平方公里,廣袤雄渾,是我國最大的內陸鹽湖。聽說逢著晴天,碰巧了,鹽湖上還能看到神秘的蜃景。我沒有觀賞到這種蜃景,卻看到了鹽湖築路戰友的情操美!
這裡與我想象的情景相差甚遠,並不是一個銀色的世界雕刻。千百萬年以來,黃沙被漠風捲進鹽湖,與滷水如膠似漆地混合在一起,形成了堅如岩石的大鹽蓋。一塊塊鹽殼皺紋般爬滿湖面,荒漠般蒼涼。沒有一棵樹、一棵草,沒有一滴鳥鳴,一滴淡水,卻要在鹽殼上架橋築路。鹽湖上不僅有高原反應,還有高濃度的鹽硝大量蒸發,對人體、物資腐蝕得相當厲害。不到三個月的時間,嶄新的棉帳篷就被咬得像紙一樣,用指頭一碰,會落下一大塊。要駐紮下來,就得因地制宜。住帳篷不行,就逼著他們想辦法,用“鹽巴磚”造房。大家用鋼釺撬,大錘砸,採回了20多萬塊鹽巴磚。然後就地挖洞鑿眼,舀滷水當沙漿,砌起了鹽巴圍牆,鹽巴禮堂和15棟鹽巴宿舍。為了減少鹽硝的腐蝕性,鹽地上墊了沙石,鹽牆上釘了蘆蓆,還糊上了幾層報紙。乍一看,還挺像一回事呢!千里鹽湖,最“壯觀”的還數連隊的“鹽巴禮堂”,足夠容納200多人。開啟蘆蓆門,裡面黑洞洞的,估計白天也能放電影。施工連隊多是三班倒,有這座“鹽巴禮堂”,上夜班的同志也可以看電影了。
現在列車駛過察爾汗鹽湖,旅客會驚歎“萬丈鹽橋”的奇觀,卻不知這是鐵道兵部隊用生命鑄造的晶體長城雕刻。“鹽殼下有二十米深的滷水,機械陷進去會化成鐵水!”一位老兵攤開掌心,滷水咬傷的裂痕如溝壑縱橫。部隊首創“以砂治鹽”的措拖:五萬立方米砂石灌入鹽湖,七萬根擠密砂樁扎進滷水,硬是在流動的鹽蓋上托起鋼軌。這得益於在施工實踐中,工程師們別出心裁地提出“擠密砂樁法”。有一位班長還改革了這種機械,成倍的提高了工效。他愛人千里迢迢趕到連隊探親,這位“革新迷”班長竟未歸屋,陪著砂樁機折騰了三晝兩夜,硬是把革新弄成了,還立了三等功……戰士們駕駛著特製的振動沉管裝置,在滷水浸泡的鹽沼中艱難作業。滷水腐蝕皮膚,強烈的反射陽光灼傷眼睛,空氣中瀰漫著苦澀的鹹腥。可當第一列試驗列車安全駛過這段由數十萬根砂樁托起的“浮”在滷水之上的路基時,整個鹽湖工地沸騰了。汽笛長鳴,宣告著人類在極端環境下創造的又一個奇蹟。
回望這846公里“天路”,耗去整整二十六載光陰雕刻。從1958年初探凍土層到1984年全線貫通,鐵道兵部隊以巨大的犧牲,在青藏高原立起世界鐵路建築史上的豐碑。

南疆長卷雕刻:在風沙中繪就鋼鐵長虹
天山南麓,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雕刻。南疆鐵路吐魯番至庫爾勒段,延伸在戈壁、荒漠與天山餘脈的交錯地帶。這裡乾旱少雨,夏季酷熱如爐,冬季寒風如刀,四季風沙不斷。鐵道兵第五、第六師的官兵們,用堅韌的意志,在風沙中雕刻著鋼鐵脊樑。
哪裡的鐵路難修,哪裡就有鐵道兵雕刻。這裡的確需要一條鐵路,蘭新線該向南疆延伸,依託天山佈局,大展宏圖,讓火車一路呼嘯,托起千年夙願。的確等不得了,萬事之急都像火燒眉毛,搞活天山,就要這種氣魄!
吐魯番至庫爾勒沿線,地形地質和氣候複雜雕刻。漫流、泥石流、大斷層處心積慮地設險,區域性地段還藏著石膏、鹽鹼,更有白楊河、克爾鹼地處風口,沙暴襲來能掀翻軍營的帳篷,卻吹不散戰士們不捨的追求。這裡的戈壁沙漠抱著45℃的高溫,還有零下三四十度的冰達坂,而風口常年颳著七八級大風,鐵路要穿越天山峽谷,開鑿一條條穿山隧道。
眼前的奎先達坂隧道已經鑿通,可我知道:這裡地質複雜斷層多,裂隙滲水源源不斷,還有730米線路困在多年凍土層,岩石裂隙中夾著冰碴,製造一次次驚心動魄的塌方,而空氣很難完全爬上這個高度,不得不頂著缺氧帶來的痛楚雕刻。1976年2月的塌方事故中,副排長周玉國把最後一個氧氣面罩塞給新兵。當戰友們扒開碎石時,發現他仍然保持著託舉的姿勢。這個湖南東安籍的青年,口袋裡還裝著未寄出的家書,字裡行間滿是對未婚妻的承諾:"等鐵路通了,帶你坐第一趟火車看天山"。回望長達6152米的奎先隧道,在艱難的掘進貫通施工中,有47名年輕的官兵長眠在天山腳下。隧道每掘進120多米,就會新增一名烈士。我脫下軍帽,朝著隧道口含淚三鞠躬……
還有著名的“百里風區”,每年八級以上大風超過200天,最大風速可超過40米/秒,飛沙走石,遮天蔽日雕刻。搭建帳篷成為奢望,戰士們只能挖掘“地窩子”——一種半地下的簡陋居所。即使這樣,一場大風過後,地窩子門口也常常被流沙掩埋大半。清晨醒來,被褥上、頭髮裡、甚至嘴裡都灌滿了細沙。炊事班蒸饅頭,籠屜蓋要用繩索和重石死死壓住,稍有不慎,連饅頭帶籠屜都會被狂風捲走。通訊兵小李,在一次搶修被大風颳斷的電話線時,被狂風裹挾著摔下山坡,幸而被一叢堅韌的紅柳掛住。獲救時,他滿身沙土,軍裝被撕破,卻緊緊抱著那捆寶貴的通訊線。風沙在他年輕的臉上刻下粗糲的痕跡,他卻笑著說:“風再大,也吹不斷咱們的‘神經線’!”
在焉耆盆地鹽漬土路段,地表白茫茫一片,踩上去鬆軟下陷雕刻。澆築混凝土基礎,鹽分腐蝕是致命難題。技術員們反覆試驗,摸索出“淡水沖洗+隔離層+抗鹽水泥”的綜合方案。戰士們頂著烈日,用珍貴的淡水一遍遍沖洗地基,鋪設厚厚的油氈隔離層。汗水滴落在滾燙的鹽鹼地上,瞬間蒸發,只留下淺淺的白色鹽漬。當第一根灌注樁在鹽鹼地深處成功凝固,標誌著這條穿越“死亡之海”邊緣的鐵路,終於擁有了堅實可靠的根基。風沙中傳來的打樁聲,是獻給荒涼與孤寂中不捨開拓者的牧歌。
這次,我真是一個團一個團的走訪南疆線,然後回五師師部所在地阿拉溝過八一節,幾位文學愛好者一齊舉杯朗誦鐵道兵雕刻。剛剛走完南疆線,風雨冰雪都在詩句裡坐胎。我們想朗誦出戰士的聲音,叫鋼鐵碰撞成詞語,在心裡鑄就兵魂。那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啊,我們一邊流淚,一邊喝酒,一邊誦讀滾燙的詩句,一邊說掏心窩子的話。只有在鐵道兵隊伍裡待過的人,才把情誼融入骨頭裡,血液裡,一輩子的親。這是我在當兵歷程中,過得最愜意的一個建軍節。
曾經當過鐵道兵——永遠的光榮
當汽笛聲在成昆線的深谷中悠然迴響,當列車滿載木材駛出嫩林線的林海雪原,當襄渝線上鋼鐵巨龍穿梭於秦巴腹地,當青藏高原的凍土上飛馳起時代的列車,當南疆的風沙戈壁被鋼鐵長龍所貫穿,那些曾經迴盪在群山之巔、風雪林海、激流險灘、生命禁區、浩瀚戈壁的號子聲、風槍聲、爆破聲、打樁聲、乃至那些犧牲戰友訣別的輓歌,並未在記憶裡消散雕刻。
所有的這些故事,都匯聚、沉澱、昇華,融入錚錚鋼軌的金屬光澤,滲入道釘靜守的堅固,銘刻在每一座橋樑墩臺的肌理,最終融入大地上最深沉、最雄渾的中國工業化“序歌”裡雕刻。這章“序歌”,是民族精神在特定時空下迸發出的璀璨之花,是鐵道兵以血肉之軀在共和國版圖上刻下的永恆印記。
鐵道兵部隊的番號已成歷史,鐵道兵戰士的身影漸行漸遠雕刻。然而,每一條延伸的鋼軌,都是我們生命的延長線;每一列飛馳的火車,都在續寫著我們用熱血譜就的序章。大地為琴,鋼軌為弦,車輪滾滾,奏響的是不滅的忠魂與一個民族面向未來的永恆之歌——這首歌裡,有山的巍峨,有河的奔湧,有風的呼嘯,有血的熾熱,更有一種穿越時空、生生不息的力量,提醒著後來者:前進的道路,從來都是由最堅韌的意志和最無私的奉獻所鋪就。
我們的隊伍以呼嘯的青春,在祖國版圖上刻下縱橫的鋼鐵血脈雕刻。操槍可以上戰場打勝仗,拿鎬能在崇山峻嶺、凍土荒漠中承擔關乎民族氣脈的重任。鐵道兵——這鋼鐵鑄就的名字,在成昆的絕壁、嫩林的極寒、襄渝的激流、青藏的生命禁區、南疆的浩瀚風沙中,譜寫出一曲蕩氣迴腸的凱歌,抒寫出一部以生命丈量大地、以意志熔鑄通途的宏大史詩。鐵道兵部隊不僅在祖國大地織就鐵路網,還以經久不衰的鐵道兵精神為標誌,貢獻出豐厚的文化食糧。
我聽見蹄聲踏踏,整個春天正策馬而來雕刻。這時,該可以和戰友們一起自豪地說:曾經當過鐵道兵,是一生的光榮!

編輯雕刻:夏天